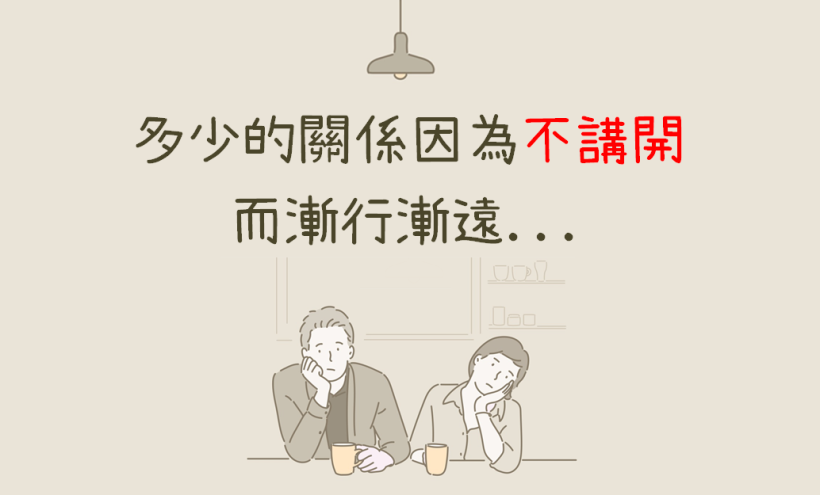
(圖片來源:shutterstock)
她是我最早的玩伴,年少的密友。
十幾歲的年紀,我們趴在桌上聽歌猜曲,
聊心儀的男孩,碎碎念著昨晚的電影;
她左手捧奶茶右手搭我肩,
跳跳糖在嘴裡噼裡啪啦。
六月的清晨、七月的月夜、八月的傍晚。
一起交過心換過帖拜過把子;
一起吐槽數學課,遲到過也罰站過;
一起跑遍杭城的大街小巷,
看電影、說胡話、淋雨或發呆。
但女孩們的友誼,都想過千百次絕交。
後來我換了新同桌,
平時上課抄作業,對她有些冷落。
因為在氣頭上,她話越來越少,
放學後也自顧自走。
我倆都是犟脾氣,
就算鬧彆扭,也拉不下臉。
既怕坦露自己的感受,
又盼著對方開口言和;
既想打破眼前的窘局,
又怕被冷嘲或熱諷。
就這樣,疏遠換疏遠,不知怎麼就淡了。
關於她的記憶,
成為壓在抽屜最底部的小紙條,
和泛著黑黃起著毛邊的大頭貼。
“來年陌生的,
是昨日最親的某某。”如果說,人和人之間,
是無數個小宇宙互相碰撞的結果。
就像赤手捧著一汪水,
也不知何時何地,
水就從指縫間流走了。
曾喜歡過一個男孩,
給自己取個瑪麗蘇的綽號,
床頭的牆角寫滿心意。
但那種“凡事全靠猜”的關係,
帶著憂慮,帶著祈盼;
帶著埋怨,帶著強求。
明明遠在異地,好不容易見上兩回面,
總是莫名其妙的黑臉、冷戰、鬧彆扭。
一次次試探和猜疑中,耗盡耐心和溫柔。
“昨晚跟他發消息,
一直都沒回音,
總不會跟別人喝酒聊天吧?”
“他越來越不主動了,
是看我不順眼嗎?
還是有什麼事瞞著我?”
我心裡住著一個小劇場。
無數次光怪陸離的小橋段,
內心戲裡自導自演。
因為凡事往最壞的地方想,
只會瞎猜,不願多問。
甚至沒有勇氣去體諒,去自證。
一旦陷入對峙關係,就像患了“疑心病”。
等著他來參透我的想法,
等著他來討好我的悲喜。
原本雞毛蒜皮的小事,
被蒙了灰,挑了刺,積壓在心底。
要不了多久,
他棄甲而逃,我逐他出局。
忘掉外在的一切標籤,
只關注眼前這個活生生的他或她。
這兩年,
有很多跟自己擰巴的瞬間,
也有很多猜錯人、會錯意的時候。
交往之初,總是先入為主去懷疑,
去揣測——卻忽略了,
誤會遠比陷阱多得多。
去年在雜誌社上班,
聽到鄰桌提起主編,
“她是個暴脾氣的狠角色,
心思重,你少惹為妙。”
故一直如履薄冰,
能少說幾句,就絕不多言。
後來分到一個小組,
在交稿、改稿的過程中,
才漸漸熟絡起來。
發現她其實是個大大咧咧,
性情真摯的朋友。
卻在造謠跟風者的口中變了模樣。
那些左右逢源,
在一群男人中間混到風生水起的“交際花”;
看似忠厚老實,
背地裡不知打著何等的小算盤的“馬屁精”;
表面上嘴尖牙硬,
實則沒立場沒底線沒啥能力的“怕事鬼”…
是真是假誰又知。
不瞭解情況就隨意評價他人,
看到冰山一角就自以為知曉全貌。
這樣的“觀人術”最為可怕。
更遑論,
很多所謂的人際隔閡,
其實是臆想出來的。
我所能做的是:
忘掉外在的一切標籤,
只關注眼前這個活生生的他或她。
與此又猜又嫌,
不如閉口不言。
越來越喜歡一個詞,
叫做“灰度思維”。
每個人都要學著,
從被情緒佔領大腦的小孩,
變成隨心不逾矩的大人。
若是認知能力越高,
對世界的理解就越灰度,
換言之,就是不黑不白。
小時候害怕跟有鋒刃的人打交道,
生怕來者不善,一不小心被扎傷;
長大後才知道相處用腦不用嘴,
看的順眼,處的舒服,便能做朋友。
電影《伯德小姐》裡有一幕,
女主角從小叛逆魯莽,選擇逃離故鄉。
她和母親針尖對麥芒,
在機場裡不歡而散。
卻不曾看到,
母親狂奔回航站路,哭花了妝。
當她獨自來到紐約,
成為無枝可棲的異鄉人。
打開行李箱時,翻到一封未完成的家信:
“我在 42 歲時,才有了你…
邁入中年,以為一輩子就這樣了。
懷你時候簡直是個奇蹟……我愛你。”

台中可樂酒店經紀
台中可樂娛樂經紀公司 ::禮服酒店::便服酒店::理容KTV::舞廳::打工兼職
台中可樂酒店經紀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(0) 人氣()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